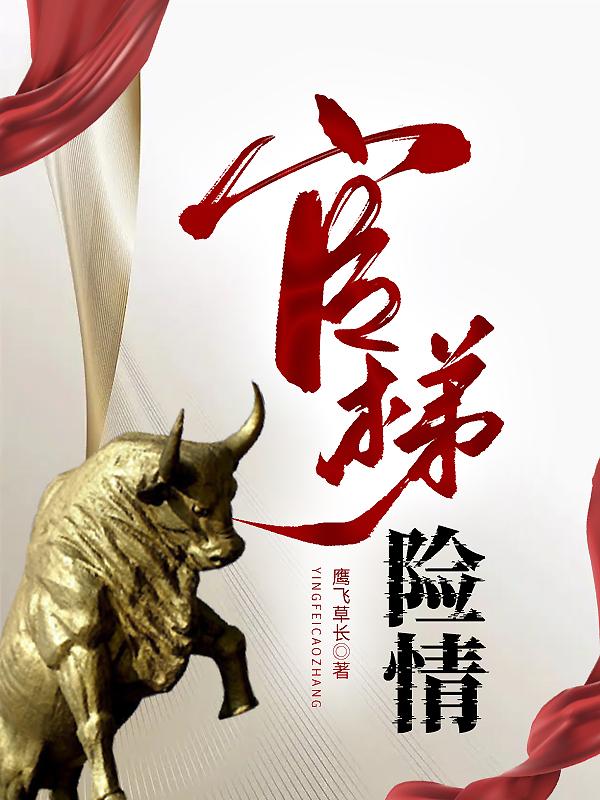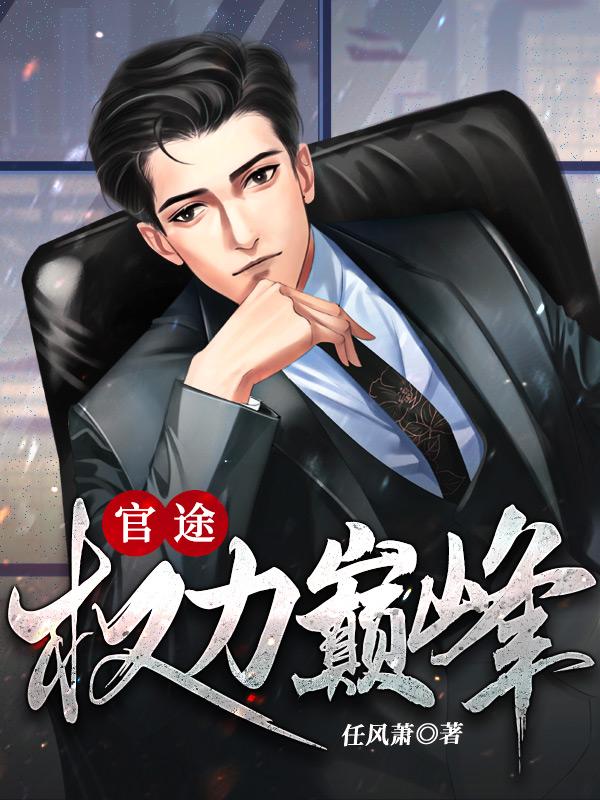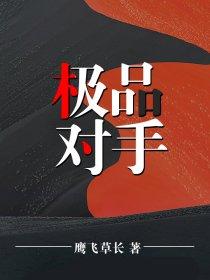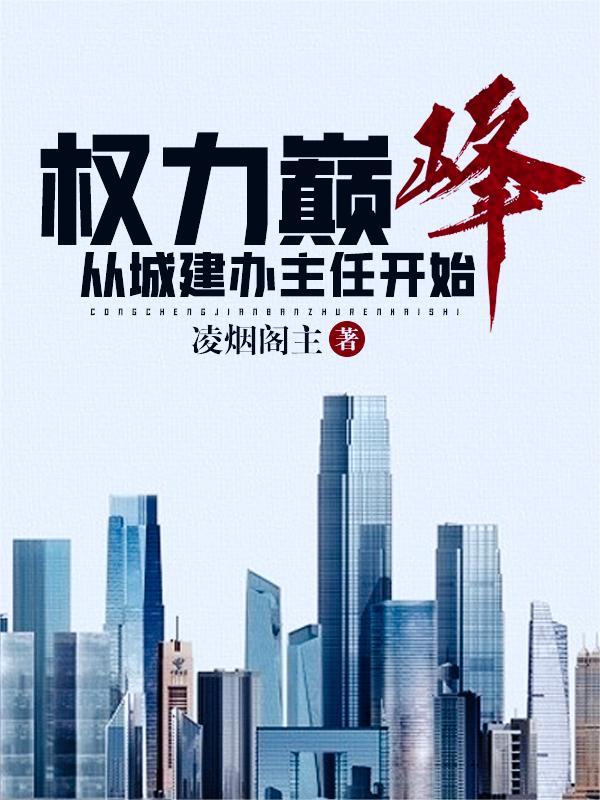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
第135章 烤火记忆(第3页)
冬日的早晨,当炊烟散尽、水缸挑满、鸡鸭喂饱、猪食进圈,村民们的冬闲时光就开始了。
墙靠墙的屋檐下,大家开着玩笑,打着招呼,慢走慢回地串着门,慢到与农忙时的风风火火彻底划清了界线。
母亲手上织着毛衣,脚步缓慢地出去凑热闹了。
年少的我们觉得,大人烧火有神一样的“功力”
,而我们则像那学艺不精的“小徒弟”
。
母亲边伺弄着灶膛里的火边说,烧火要注意方法,别急躁,做事要有耐心,我们似懂非懂的点着头,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,没有丰富多彩的零食,家里种的红薯或蒸或晒,都吃腻了的时候,烤红薯和土豆就特别有诱惑力了。
当红薯从灶膛落到灶台上时,我们急切地跨步贴近了灶台,手不由地伸向了红薯,滚烫之下,手指在红薯上一伸一缩,急不可待。
馋嘴的模样,大概红薯都知道,我们烤火是为了烤它、吃它,它与烤火是绝配,火唤醒了它那内在的灵魂香味。
撕开粗皱的表皮,颜色鲜黄,热气升腾,满屋飘香,咬一小口,甜丝丝、软糯糯;咬一大口,甜糯里夹了柴灰;一个咬完,嘴角两边像黑、黄彩笔上了色,放到现在就是不讲卫生的典型,会与细菌、病毒挂上钩。
但,那个年代的孩子,那句“不干不净,吃了没病”
喊得还真不是口号。
我们小时候顶多见过几回赤脚医生。
冬天烤火不吃烤红薯,那都是一个遗憾,烤红薯甜美了年少时的烤火时光。
天气虽冷,但心里却是暖暖的。
所以,年少时的烤火时光,是我们小时候最踏实,也最温馨的时光。
到了晚上,母亲搬出了火盆,烧燃了木炭。
昏黄的灯光下,一家人围坐在火盆边,母亲依旧织着毛衣;闪着点点雪花的黑白电视机,父亲在摆动着手摇天线;我们两眼期待地望着黑白电视机那跳闪的屏幕,它闪一下,我们心里跳一下,心情跟着屏幕七上八下,画面稳定下来,心也跟着平静下来,这时炭火也燃烧得刚刚好。
柔和的温热,从脚底慢慢上升到了头顶,那一刻,炭火与时光相融在了一起,暖得忘记了冬天的寒冷。
相比于柴火,木炭火显得温顺、平和、易掌控。
柴火像个脾气火爆又粗鲁的男子,炭火像个温和又听话的女子。
那个年代的冬天,晚上烤着炭火,看着电视,心里是满满的惬意。
当然,惬意是小孩子的感受,那时年少的我们,还不懂生活的艰辛,不懂现实的无奈,大了一点才知,木炭是要花钱买的。
于是也就想起了,每年的冬天,都有人挑着木炭来村里卖,围观之下,是卖炭人和村里买炭人讨价还价的声音。
用炭火的时间还是少数,因为炭火不熏人,大部分时间还是选择在外面捡野材来烧,米云记得家里只烧过三五回木炭,不知道哪里来的木炭,后来就再也没用过了,只要勤快点,到外面都能捡回一大堆柴火。
随着时代的发展,农村人的生活渐渐好转,到了九十年代,烤火的时光里,烧的已是蜂窝煤,我们家乡叫煤球。
生活向前跨了一步,烤火的方式也跟着前进了一步!
煤球解决了天天烧火的麻烦,像一个成熟起来的青年人。
只要我们用正确的方式与它相处,第二天早上等着我们的还是一炉温暖。
烤火时,无需像柴火、炭火那样,时时注意火势,注意添柴加炭。
但是,它却不能像柴火、炭火那样烤红薯了,方便的同时少了童年的乐趣。
最初的火炉没有烟管通向窗外,刚燃起的煤球散发着刺鼻的气味,通风不良的话有煤气中毒的风险,所以,天气再冷,家里的窗户也会有一扇是打开的。
九十年代后期,烤火桌、烤火罩盛行起来。
火炉算是有了标准的配置,烤火变得更舒适,更温暖了。
烤火的时光里有了麻将声,电视换成了彩电。
邻居们串门更多的是约麻将了。
往后,我们成年,离开了家乡,对于家乡烤火时光的记忆好像更多的是停留在了年少时。
- 潘多拉的复仇一颗仔姜
- 无敌从觉醒武器大师开始乾上乾下
- 怎么都想欺负恶毒女配梦境小鱼
- 七零宠婚:撩硬汉!生三胎酥幽田
- 纸飞机(校园 青梅竹马 1v1)琂
- 被嫡姐换亲之后明春鸢
- 见微知著(弟妹 H)乱佳音
- 鱼目珠子(高干1v1)崽崽猎手
- 含泪做1小檀栾
- 大王万万不可!你的荣光
- 黑心大小姐带着空间下乡啦青橘柠檬茶
- 琉璃阶上尤四姐
- 重生表白失败,校花急了水果饺子
- 天仙师娘不醉
- 伪装大佬那些年魏朝瑾
- 没你就不行之新征途林木儿
- 男主怀了我的崽顾西子
- 当明星从跑龙套开始青丘千夜
- 以婚为名茶衣
- 替身男配只想赚钱时今
- 龙凤猪旅行团珠玉在前
- 龙傲天的反派小师妹飞翼
- 误入官路陈酒
- 嫁给铁哥们衣落成火
- 下乡的姐姐回来了清澜皓月
- 官道之权势滔天赵小二
- 偏偏宠爱藤萝为枝
- 官途,搭上女领导之后!平和心境
- 在北宋当陪房金鹅
- 非常权途沧海而立
- 娱乐春秋(加料福利版)姬叉
- 云婳谢景行三尺神明
- 听说你暗恋我久久
- 大王万万不可!你的荣光
- 替嫡姐爬上龙床,她宠冠后宫苏漫漫
- 官梯险情鹰飞草长
- 官路扶摇雪路听花
- 就职供销社,我在60年代搞代购酱汁炒饭
- 六零之走进四合院女王不在家
- 官场:扶摇直上九万里火了买飞机
- 官场之狐江南老六
- 夫郎弱小可怜但能吃菇菇弗斯
- 千里宦途小豌豆本尊
- 梨汁软糖【1V1甜H】吃甜少女
- 官场:救了女领导后,我一路飞升叁叁伍伍
- 官路红途小冬瓜瓜
- 癌症晚期,前任女友疯狂报复我半城清梦
- 四合院之我是猎人土豆三条
- 神祇觉醒:谁说东方没有神明?沫随
- 官路浮沉争渡
- 和死对头冥婚后,我俩一起诈尸了酸菜鱼多加辣
- 狗尾巴番茄肥牛子
- 诡秘复苏:从傩戏开始长生紫色孤魂
- 仙剑镇魔录风花雪意
- 花都神医风云九鬼
- 功法太强,女帝采补遭反噬五月落霞
- 贬妻为妾?她搬空渣夫库房高嫁权臣唐宝er
- 医道无双,狂撩高冷女富婆狼性佛心
- 暗爽!他抢傅总前妻上位了将满
- 曝光历代皇帝六维图,老祖宗慌了九品大韭菜
- 全球御兽:开局觉醒每日情报系统月尽天明
- 被人杀害后复活成为道士笔名太阳
- 绝美校花悔哭了柚子太菜
- 我就卖个玩具机甲,你说这是军火?尖椒葱白
- 重生80:从赶山打猎开始暴富薛不是
- 魂殿第一玩家天空泪
- 我在仙宗当杂役,观摩万年成仙帝妤白
- 我就打个游戏,怎么电子女友成女帝了?传说是橘黄色的
- 神话降临:无限吞噬煞气,肉身成圣!且行徐
- 太子妃无嗣?简单,我帮她不就行了逸辰风
- 双叶逆仙西瓜刨冰
- 孤岛春夜宴
- 我的性欲猴子同学爆肏我全家(无绿NTL改)佚名
- 我的老婆是女天帝柳江山人
- 九尾狐女友带我斩妖除魔ZZ林深深
- 攻略偏执反派又抛弃他后微我无酒w
- 我都成首富了,你才来认亲?十点三十一
- 科技在手,来个皇帝当当咯月月也困
- 高中毕业去守墓,我靠垃圾天赋横推副本!限定供应
- 神陨之日,我以扮演证神格青柠客
- 绑来战神后,恶毒女配癫疯了整个修仙界瑛霞之盼
- 冥神重生:大千世界的殓尸人章鱼小跟班
- 我的性欲猴子同学爆肏我全家(无绿NTL改)佚名
- 绑定万界拍卖行,三小姐靠赚功德升级墨色韶华
- 逆世天尊之路威廉书王
- 真神的鱼缸看到我你算是吃菌子了
- 别人末世求生,你开烧烤店躺赢?大力香菜
- 圣祖重生Zero·君怡
- 灰尘(堕落的灰尘)vampivirman(一剑潇潇)
- 枯骨生花·病娇嫡女她靠毒谋天下燕语时光